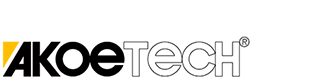期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接受了《中國電力報》、中電新聞網記者采訪,就“十三五”期間的能源問題分享了他的看法。

“補貼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補”
記者:您如何看待可再生能源在“十三五”期間的發展?
趙昌文:就“十三五”而言,可再生能源的整體比重會大幅提高,這是必然趨勢。不光在中國,從其他國家的情況來看也是這樣。但現在的確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全球能源價格的下降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客觀上產生了一個不太有利的影響,包括對天然氣,還有太陽能、風能等過去要靠政府補貼來發展的這些能源類別都受影響,既然不能永遠靠補貼,那么最終還要靠市場。
記者: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應對呢?
趙昌文:總體來說,有兩個硬約束是不能變的。第一個是環境約束,這肯定不能變。第二個是經濟的硬約束,確切說是基本規律。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經濟增速下降,需要找新的增長點。對此,我覺得至少有三點在經濟結構方面會有很大變化。一是服務業比重的上升和工業比重的下降,這是必然的,自2012年開始我國服務業增速超過了工業,服務業比重的上升本身就意味著能源需求的下降。二是在制造業或工業當中,高耗能產業比重下降,而高加工度的工業、高技術產業比重上升。三是在傳統的高耗能工業內部,能源效率會有所提高。總之,以上經濟層面的三種結構變化加上環境硬約束,使得可再生能源在“十三五”期間比重上升是必然的。
記者:在需求寬松的情況下,清潔能源如何保證其比重的上升?
趙昌文:實際上這是個博弈。從宏觀上看,我們希望有更多的藍天、白云和清潔空氣,自然希望清潔能源比重越高越好。但從短期看,價格差距是客觀存在的,所以過去清潔能源要靠政府補貼,不光是在我國,德國、日本等國也這樣。我認為,全世界在發展新能源的中短期內,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政府補貼還是很重要的。要看到這個行業有一個準入門檻,如果這個門檻是因為政策造成的,政府不需要補貼,但是如果這個門檻是因為技術造成的,是因為整個行業平均的準入成本等因素帶來的,那么政府必須要補貼。
這種情況也包括新能源汽車,很多核心技術沒有大的突破,導致成本依然很高。
而在這種高成本情況下,政府如果不補貼,相當于企業的風險遠遠大于收益,那就沒有人愿意投資了。政府補貼是改變風險收益結構,從而使得企業自己承擔的風險加上政府補貼減少的風險能夠匹配整個風險收益結構,一是從價格空間上去匹配,二是從時間周期上去匹配,最終才能帶來新能源行業的發展。所以,在一段時間內我覺得有必要堅持補貼。
記者:是不是問題的關鍵在于怎么補?
趙昌文:對,談論補貼問題的關鍵不是需不需要,政府怎么補才是最重要的。這里還有個是補供方還是補需方的問題。
從供方來說,政府還需要有政策,鼓勵企業去進行技術創新,我覺得供方的技術創新還是需要政策繼續支持的。但是從更多層面看,實際上將來要逐步減少對供方的補貼,而且杜絕企業變成套利者、機會主義者類似的不利于行業長期發展的現象。
從需方來說,因為基本改革方向就是市場化,不管是新能源還是傳統能源,最終體現的都是能源,不同能源有不同價格也不合適,所以很多政策也得改革。我覺得現在天然氣領域交叉補貼還挺嚴重的,那將來還是要改的。一個就是要實現工商業用氣價格完全市場化,要有時間表和路線圖。
至于居民交叉補貼問題,近來北京燃氣企業的工作人員來我家裝表了,開始實施階梯價格,這么看來在需方已經開始有好的變化了。
“要尊重市場選擇的結果”
記者:您對“十三五”電力消費增速有沒有預期?怎么統籌煤電和可再生能源發展?
趙昌文: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但“十三五”期間的經濟增長情況是一個基本的參照系。“十三五”期間的能源需求肯定要聯系以下兩方面來考慮:一是經濟增速,二是經濟結構變化。從整體上來說,我國提出了“雙倍增”計劃,基本上GDP年均增速要達到6.5%,那樣才能保證實現目標。從以往情況來看,能源領域投資增速實際上是快于GDP增速的,綜合各方因素預測,“十三五”能源領域投資速度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
至于如何進行統籌?我覺得是市場選擇的結果,需要尊重這個結果,靠人為很難去統籌。我覺得“十三五”期間煤電比重肯定會下降。水電方面有些復雜,我曾在雅礱江、大渡河流域看到好多梯級電站,當時建水電站都考慮著給長江中下游供電,而現在長江中下游經濟結構變化很大,重工業開始向越南、印度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所以對電的需求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地區發出的電也出現富余,畢竟電力需求不像過去那么旺盛,這些都需要考慮在內。
記者: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十三五”期間不再像以前那樣過于強調能源消費總量控制了吧?
趙昌文:我認為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什么叫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包括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實際上可以理解成一個結果,比如某一階段總的需求量、消費量下來了,就可以認為結果上好像是控制了。
實際上開始提出這個目標時,這本來就有些切換經濟思維方式。所以我認為,要有政策杠桿去引導能源結構的調整,去引導能源效率的提高。